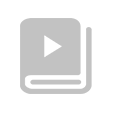摘要:间接正犯实行的着手是实行行为着手的一种特殊形态,故对此问题的研究既应以实行行为着手的一般理论为依据,还需要充分考虑其特殊性。以实行行为着手的一般特点为依据,同时对间接正犯的特殊性进行深入剖析,结合刑法的谦抑主义精神,可以得出间接正犯的着手应采纳“被借助者说”的结论。
关键字:间接正犯;实行行为;着手。
间接正犯实行着手问题是一个在刑法学界备受争议的问题,而对此问题的研究不只具备要紧的理论价值,更具备重大的实践性意义。
1、间接正犯实行着手的理论争议。
理论界关于间接正犯实行着手的倡导主要有以下几种:
“借助者说”,该看法觉得行为人开始推行借助或诱致别人的行为时,就是间接正犯的着手。因为间接正犯的正犯性,被借助者的“行为”只是间接正犯犯罪当中的一种中间现象或“中介”,其不可以称作实行行为。因此,间接正犯的实行着手也就只能存在于借助者的借助行为中。日本学者大冢仁教授觉得:“诱致(借助)行为中包括着某种现实的危险性。既然是实行行为,诱致行为也应该与普通的实行行为一样,需要包括着现实犯罪的现实危险性。”[1]该说得到了日本理论学界的广泛支持,台湾多数学者也支持“借助者说”,国内国内学者陈兴良教授也赞成该说。
“被借助者说”,即被借助人开始推行风险行为之时才是间接正犯的实行着手。该说觉得,在间接正犯的场所,借助者的借助行为因为没办法形成对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性,多只不过犯罪的预备行为,只有被借助者现实进行的身体动静,才是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所以,也只有被借助者开始进行作为被借助的工具的身体动静时,才能认定为间接正犯的着手。弗兰克觉得:“间接正犯是借助中介者进行犯罪的形态,因此,其实行的着手不可以早于中介者的着手。”[2]该说得到了日本的判例、少数学者及德国通说的同意。
“个别化说”,此说觉得在通常情况下,以借助者开始推行借助别人的行为时,即为间接正犯的着手;而借助有有意的工具的间接正犯则以被借助者开始身体活动时,即为间接正犯的着手。
“借助者说”完全没把握间接正犯的实质和特点,也没理清实行行为着手的一般理论。把借助人开始借助的行为牵强附会地理解为间接正犯的着手,实难具备说服力。而“个别化说”试图依据间接正犯的具体情形进行实行行为着手的个别化剖析,这种思路虽然符合具体问题具体剖析的办法论,对间接正犯实行着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其缺少理论的一贯性,破坏了实行行为的统一性,也不足可取。相比较而言,“被借助者说”更具备合理性,下面将从不一样的方面进行讲解。
2、“被借助者说”之论证。
(一)“被借助者说”符合实行着手的一般理论间接正犯的实行着手,是实行行为着手的一种,其应当符合实行行为着手的一般理论。实行行为的着手是指行为人基于犯罪的故意,开始推行刑法分则规定的具备法益侵害的紧迫危险性行为。“被借助者说”符合实行行为着手的一般特点。
1.从主观方面考虑,对于着手实行犯罪的人来讲,其意志是以直接推行犯罪为目的,并且已经通过客观实行行为的开始充分表现出来,而不同于此前预备实行犯罪的意志。犯罪预备反映的主如果行为人预备实行犯罪、为推行犯罪创造各种各样便利条件的故意。至于具体推行犯罪的主观设计构思,行为人当然具备,但这种故意在预备阶段还没得到具体推行和展开,还只不过在预备行为中间接地得到表现。而着手实行犯罪的行为人,其犯罪故意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其主观心理状况的期望已经从“期望预备行为顺利完成”到“实行行为顺利完成与风险结果的发生”。显然,这是着手实行犯罪和预备犯罪所体现的主观原因不可以简单等同是什么原因之所在。质言之,预备行为的直接目的是为犯罪创造条件;而着手实行犯罪时,行为人却是以直接推行犯罪为目的。在间接正犯中,被借助人可以理解为借助人的“活体”犯罪工具,也就是说借助人的借助行为只不过为犯罪筹备工具,创造条件,其期望被借助人可以任其摆布借助,至于具体推行犯罪的详细构思,借助人也有,但这种故意在其推行借助的过程中还没得到具体体现,只能在其借助过程中隐约地体现出来。借助人的借助阶段是以为具体推行犯罪创造条件为目的的,因此,借助者的借助行为只不过犯罪的预备阶段,而不可以理解为以直接推行犯罪为目的的着手阶段。当被借助者作为借助者的犯罪工具开始推行具体的犯罪行为时,借助者就是以直接推行具体犯罪为目的。从这方面看,间接正犯的实行着手只能存在于被借助者的行为中。
2.从客观方面考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着手实行犯罪的行为已经同直接客体发生了接触,或者说已经逼近了客体,在有犯罪对象的场所,这种行为已经直接指向犯罪对象。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应当是被法律所定型化了的具备法益侵害性的现实而紧迫的危险行为。比如,故意杀人犯已经举起刀对准了被害人,这表明其杀人行为已经开始现实地指向了客体,并且直接危及客体的生命安全,法益遭到了现实的、紧迫的危险。在间接正犯中,借助人对被借助人加以教唆、引诱的行为,还并没接近直接犯罪客体,还不可以对法益导致现实的、紧迫的危险,只有当被借助人开始推行借助人所诱致的具体犯罪行为时,犯罪客体才有了现实的、紧迫的危险性。第二,着手实行犯罪的行为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客观方面需要的行为,应当借用于国内刑法分则关于各罪的规定对借助者定罪。
一般而言,对间接正犯的定罪是以被借助者的定型行为入手的。比如,通过无责任能力的人推行偷窃行为的,被定为偷窃罪。可见,被借助者推行的这种符合刑法分则定型化了的盗取别人财物的行为,是间接正犯定罪的依据。而借助者的借助行为阶段还不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定型化的犯罪的客观方面的需要,因此,实行行为的着手也无从谈起。
(二)“被借助者说”符合间接正犯的特殊性。
间接正犯实行着手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实行着手,其除去应拥有实行行为着手的一般特点外,还具备自己的特殊性。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间接正犯实行着手才看上去扑朔迷离,以至于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分歧,也产生了对“被借助者说”的各种质疑。
针对质疑,笔者预发表自己批驳性的拙见,以否定之否定的办法证明“被借助者说”的合理性。
1.有人觉得,在间接正犯的被借助者中,包含像精神患者一样不可以推行刑法意义上的“行为”的人,这种被借助者的身体动静不是行为,按理就不可以认定为实行行为。因此,间接正犯实行着手只能存在于借助者的借助行为中。但,间接正犯的本质特点就是其正犯性,被借助者只不过借助者的“活体”犯罪工具,其推行犯罪的身体动静应被视为借助者肢体的延伸而亲自实行的犯罪行为。大家不可以仅仅看间接正犯实行行为形式意义上的特点,以偏概全地觉得假如同意“被借助者说”就是承认包含精神患者在内的被借助者的行为具备实行行为性。因此,“被借助者说”并没摒弃传统刑法理论———精神患者推行的行为不具备刑法意义上的实行行为性,而是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进步。
2.有学者提出,假如以“被借助者说”来认定间接正犯实行着手,那样实行的意思和实行的行为就分是不一样的主体了。这种质疑的目的在于保持刑法基本理论的统一性和连贯性,出发点是值得称道的。但,依据上文所提到的,在间接正犯中,被借助者只不过借助者的犯罪工具,其推行犯罪的行为应视为借助者身体行为的自然延伸,被借助者推行的害处行为应被视为借助者的实行行为。实行行为主体应被视为是借助者,当然,意思主体也是借助者,实行行为主体与意思主体都是借助者,并没违背刑法理论的有关原则。
同理,关于“被借助者说”违背“违反行为与责任主体同在”的原则的言论也就不攻自破了。间接正犯实行行为最大的特殊性就是被借助者只不过借助者的“活体”犯罪工具,被借助者推行的害处行为应被视为借助者自己行为的自然延伸。看到这一点,间接正犯实行着手就简单明了了,所有些质疑也都迎刃而解了。
(三)“被借助者说”体现了刑法的谦抑主义精神。
无论是从实行行为着手的一般理论来看,还是从间接正犯的特殊性考察,“被借助者说”都是最适当的选择。除此之外,与其他倡导相比,被借助者说还体现了刑法的谦抑主义精神。根据“借助者说”、“个别化说”的倡导可能致使的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将实行行为的着手过于提前,“无疑都会扩大处罚范围,把犯罪预备当做犯罪未遂处置,与刑法的谦抑主义精神相背而行。”[3]依据“借助者说”,只须行为人向他们说:“将其他人的财物拿来。”即便他们根本没偷窃,行为人偷窃未遂也成立,如此就扩大了未遂犯处罚的范围。有人觉得:“只须推行借助行为,就征表出行为人的危险性格,应当处罚。”[4]而且,国内《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关于教唆未遂的规定就是对以上看法的有力支持。法律规定被教唆的人没推行被教唆的罪,教唆者依旧成立教唆未遂,而对于与教唆犯相类似的间接正犯而言,即便被借助人并没推行风险行为或者推行了其他风险行为,借助者的借助行为依旧成立未遂犯。但笔者觉得:
第一,依据刑法禁止类推的原则,大家不可以以教唆犯与间接正犯有几分相似就以一个实然的问题去证明一个应然的问题。第二,国内《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本身就存在问题。法律特别是刑法只能规范人的行为而不可以左右人的思想。人性本身就具备不可防止的脆弱性和恶的一面,“只须推行借助诱致行为,就体现了人的危险性格,应当处罚。”显然是对人性提出了过于苛刻的需要,这种试图使人成为天使的想法未免太过于纯真无邪和不切实质了,这与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谦抑主义精神是不相符合的。而“被借助者说”将间接正犯的实行着手限定在被借助者的行为中,防止了将间接正犯的实行着手过于提前的问题,相对于其他倡导而言,其将间接正犯的未遂控制在被借助者行为的阶段,大大缩小了未遂犯的处罚范围,体现了刑法的谦抑主义精神。
3、结论。
综上所述,在间接正犯中,被借助者是借助者的“活体”犯罪工具,借助者的借助行为只不过为实行犯罪筹备工具的行为,在本质上是犯罪预备行为。只有当被借助者推行身体活动时,法益侵害的危险才能定型,才具备现实的、紧迫的危险性,才可能被评价为犯罪的实行行为,认定为实行的着手。被借助者的害处行为应被看做是借助者肢体活动的自然延伸,实质是借助者的实行行为。
参考文献:
[1](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M].冯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87.
[2]西原春夫。犯罪实行行为论[M].戴波,江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01.
[3]吴飞飞。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研究[J].延边大学学报,2005, (9)。
[4]张明楷。未遂犯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6